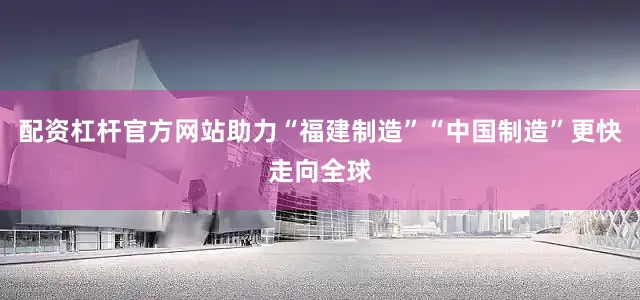老话常讲:“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
人生在世,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棋盘。
有的人,终其一生都是别人棋盘上的子,随波逐流,身不由己,被人拿捏,被人算计,最终落得个“鸟尽弓藏,兔死狗烹”的下场。
而有的人,却能洞悉棋局的走向,看透人心的变幻,最终从一颗无足轻重的棋子,逆袭成为执棋的布局者,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这其中的差别,究竟在哪里?
很多人以为,在于“城府”。
他们觉得,只要心机够深,手段够狠,喜怒不形于色,就能在复杂的世事中立于不败之地。
于是,他们学着伪装,学着算计,把心包裹得严严实实,把脸雕刻得毫无波澜。
然而,这样做的人,往往活得最累,也最容易陷入更大的困局。
因为,真正的权谋,从来不是靠阴暗的伎俩,而是源于阳谋的智慧。
两千多年前,那位忍受着世间极致的屈辱,却写下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的司马迁,早已在一部《史记》中,将这其中的奥秘点透。
他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,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,告诉我们:真正的权谋,不在于城府多深,而在于“趋利避害”这四个字。
这四个字,看似简单,却是人间最高级的智慧。
它不是让你去钻营苟且,趋炎附势,而是让你看清利益的流向,避开无谓的灾祸,从而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,找到那条通往成功的最佳路径。
读懂了这四个字,你便能从被动的局中人,一步步成为主动的布局者。

利之所趋,人之所向:看清利益,是布局的第一步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有言: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”
司马迁一针见血地指出,驱动世间万物运转最底层的逻辑,就是一个“利”字。
这个“利”,不单单指金钱财富,更包括了地位、名声、权力,甚至是他人的认可与情感的满足。
看不清利益的流向,就如同在黑暗的森林里蒙眼狂奔,你所有的努力,都可能是在南辕北辙。
权谋的本质,不是凭空创造规则,而是顺应并利用已经存在的规则。
而“利益”,就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规则。
所谓布局,第一步就是要看清楚局中每个人,包括你自己,最核心的利益诉求是什么。
这一点,汉初的张良,堪称典范。
在楚汉相争的鸿门宴上,杀机四伏。
项羽手握四十万大军,范增谋划周密,刘邦如同砧板上的鱼肉,生死只在项羽一念之间。
当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刘邦的生死上,但张良却看到了更深层次的利益链条。
他知道,对于项羽而言,最大的利益是什么?不是单纯地杀死一个刘邦,而是成为名正言顺的“天下共主”。
直接杀死已经投降且愿意称臣的刘邦,会落下一个“杀降不祥”的残暴名声,这与他“西楚霸王”渴望建立的威望和道义是相悖的。
这是项羽的“名利”。
他又看清了项羽阵营内部的利益分割。
项羽的叔父项伯,虽然身在楚营,但与张良有旧,更重要的是,他希望在未来的新秩序中保全家族,获得富贵。
如果刘邦被杀,唇亡齿寒,他项伯作为与刘邦私交过密的人,也难逃猜忌。
因此,保住刘邦,符合项伯的“身家性命之利”。
于是,张良没有去向项羽苦苦哀求,而是走了一步妙棋——深夜拜访项伯。
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记载,张良对项伯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,核心就是将项伯的利益与刘邦的生死牢牢捆绑。
他让项伯明白,刘邦若死,你项伯也难保平安;而若刘邦能活下来,将来必有厚报。
张良甚至当场让刘邦与项伯“约为婚姻”,结成儿女亲家。
这一下,利益共同体变得牢不可破。
第二天鸿门宴上,当范增举起玉玦,示意项羽下杀手时,正是这位项伯,一次次起身敬酒,用身体挡在刘邦面前,甚至
“拔剑起舞,常以身翼蔽沛公”,使得刺客无法近身。
最终,刘邦得以借口逃脱,为日后的翻盘赢得了最宝贵的机会。
张良的“谋”,不在于他创造了什么,而在于他看清了所有人的利益诉P.O.V.。
他准确地抓住了项羽爱惜名声的“大利”,和项伯渴望保全自身的“小利”,然后用一根无形的线,将这些利益巧妙地串联起来,最终撬动了整个危局。
这便是“趋利”的智慧。
在任何困境中,不要只盯着眼前的困难和情绪,而是要冷静地抬起头,像一个猎人观察兽群一样,去观察局中每一个人的动机。
谁渴望什么?谁害怕失去什么?他们的利益在哪里?当你能画出这样一张清晰的“利益地图”,你就拥有了布局的资格。
普通人被情绪和表象左右,在困局中挣扎;而高手,则是在人性的底层逻辑里,寻找破局的钥匙。

害之所存,避之若浼:识别风险,是保命的护身符
如果说“趋利”是进攻,那么“避害”就是防守。
在人生的棋局中,活下来,永远比吃掉对方更重要。
不懂得识别和规避风险,即便给你再好的开局,也可能一步踏错,满盘皆输。
《史记》中充满了这样血淋淋的教训。
那些才高八斗、功高盖世的能臣猛将,最终身死族灭,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,不够勇猛,而是因为他们没能看清那个悬在头顶的“害”字。
这个“害”,有时候是君主的猜忌,有时候是同僚的嫉妒,有时候是功高震主的危险,有时候,甚至是你自己无法控制的性格缺陷。
韩信,这位被后世誉为“兵仙”的军事天才,他的一生,就是对“不懂避害”最深刻的诠释。
韩信的军事才能,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足以排进前五。
他“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”,平定三秦;背水一战,大破赵军;北上降燕,东进攻齐,最后在垓下设十面埋伏,逼得不可一世的项羽乌江自刎。
可以说,没有韩信,刘邦的汉室江山,至少要晚来十年。
他的“利”趋到了极致,功劳大到了“无以为封”的地步。
然而,也正是这泼天的富贵和功劳,成了悬在他头顶最锋利的一把剑。
这个“害”,就是君主的猜忌——“功高震主”。
刘邦是什么人?一个从市井中杀出来的皇帝,他对权力的敏感和对背叛的恐惧,是刻在骨子里的。
当韩信的威望越来越高,甚至能与他分庭抗礼时,刘邦心中的警铃就已经响彻云霄了。
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中记载了多个致命的细节。
第一次,刘邦兵败彭城,狼狈逃窜,韩信却在北方战场捷报频传。
刘邦做的第一件事,是“驰入韩信壁,夺其印”,瞬间解除了韩信的兵权。
这是最明确的警告信号,告诉韩信:兵权,是我的,不是你的。
韩信若懂得“避害”,此刻就应该收敛锋芒,主动交出权力,以换取信任。
但他没有,他选择了继续领兵,继续建功立业。
第二次,韩信攻下齐国后,派人向刘邦上书,请求封自己为“假齐王”,以便于管理。
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,急需韩信的救援。
看到这封信,刘邦勃然大怒,破口大骂:
“我困于此,旦暮望若来佐我,乃欲自立为王!” 张良和陈平在桌下猛踩刘邦的脚,示意他不能发作。

刘邦这才转怒为喜,说:
“大丈夫定诸侯,即为真王耳,何以假为!” 于是封韩信为齐王。
这一封,看似是奖赏,实则是将韩信放在火上烤。
从“假王”到“真王”,韩信欣然接受,他完全没有意识到,自己已经在“君主猜忌”这条红线上,跳起了最危险的舞蹈。
他若懂得“避害”,就该在刘邦震怒时立刻请罪,表示自己绝无二心,并火速发兵救援,而不是心安理得地接受封赏。
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,刘邦登基后,先是“伪游云梦”,再次夺了韩信的兵权,将他从齐王降为淮阴侯,软禁在长安。
最后,吕后与萧何合谋,以谋反的罪名,将这位战无不胜的“兵仙”,诱杀于长乐宫的钟室之内。
临死前,韩信才发出了那句著名的感叹:
“吾悔不用蒯通之计,乃为儿女子所诈,岂非天哉!”
他到死才明白,自己不是败给了敌人,而是败给了那个不懂“避害”的自己。
他看得清战场上的千军万马,却看不清朝堂上的人心险恶;他算得出敌人的每一步动向,却算不出君主心中那杆猜忌的天平。
“避害”的智慧,不是让你变得懦弱和退缩,而是让你拥有鹰的眼睛,能从万米高空,看清地面上哪里是坦途,哪里是沼泽。
当你感到一丝危险的气息时,哪怕要放弃唾手可-得的利益,也要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。
因为,对于一个布局者而言,留得青山在,才有柴烧。
一时的退让,是为了更长远的胜利。
韩信的悲剧,是每一个职场人、每一个身处复杂环境中的人的镜子。
当你才华出众,功劳卓著时,一定要时刻自省:我是否触碰了上级的安全感?我是否引起了同僚的嫉妒?我是否因为骄傲而忽视了潜在的风险?
懂得低头,有时比懂得昂首更重要。
看到这里,你可能会想:原来如此,“趋利”是看清方向,“避害”是守住底线。
一个进攻,一个防守,掌握了这两点,不就可以纵横捭阖,立于不败之地了吗?
如果你真的这么想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这恰恰是许多自作聪明的人,最容易掉进的陷阱。
他们以为看懂了利益,规避了风险,就可以操控一切。
但他们忽略了权谋中最核心,也是最反直觉的一环。
为什么同样是功高震主,韩信死了,而另一个人的结局却截然不同?
为什么在《史记》中,有的人明明把“利”和“害”算得清清楚楚,步步为营,最终却还是一败涂地?比如那个劝说韩信造反的蒯通,他把利害分析得头头是道,韩信不听,他自己最后却差点被杀。
这背后,到底还隐藏着什么更深层的秘密?
司马迁通过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命运告诉我们,仅仅做到“趋利避害”,你最多只能成为一个精明的投机者,一个随风摇摆的墙头草,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布局者。
因为你所有的行动,都还是被动的——被“利”诱惑,被“害”驱赶。
要从被动变为主动,从棋子变成棋手,你还必须掌握另外两个字。
这两个字,是“趋利避害”的升华,是整个权谋体系的“神魂”所在。
它能让你在没有“利”的地方创造出“利”,在看似必死之“害”中,开辟出一条生路。
这,才是顶级谋略家与普通聪明人之间,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。
那么,这神秘的第三个字,究竟是什么?
因势利导,无中生有:所谓“势”,是最高级的“利”
这第三个字,就是“势”。
《孙子兵法》云:“激水之疾,至于漂石者,势也。”
湍急的流水能冲走巨石,不是因为水本身有多大力量,而是因为它汇聚了强大的“势能”。
在《史记》的权谋世界里,“势”是一个比“利”更高级的概念。
看得见摸得着的金钱、地位是“小利”,而“势”——即事物发展的趋势、人心向背的潮流、天下大局的走向——才是真正的“大利”。
一个三流的谋士,追逐眼前的小利;一个二流的谋士,懂得权衡利弊;而一个一流的布局者,他懂得“造势”和“用势”。
他能敏锐地察觉到大势的苗头,然后顺应它,推动它,甚至在无“势”可借时,创造出对自己有利的“势”,最终让“势”本身,成为自己最强大的武器。
谁是《史记》中当之无愧的“造势”大师?答案只有一个:陈平。
如果说张良是“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”的战略家,那么陈平就是那个在阴影中拨弄人心的魔术师。
他的计谋,往往匪夷所思,直击人性最脆弱的地方,其核心,就是对“势”的极致运用。
楚汉战争相持阶段,项羽强大,刘邦弱小,这是一个基本盘。
此时,项羽唯一的软肋,就是他身边最重要的谋士范增,以及钟离昧、龙且等几员大将。
项羽虽然刚愎自用,但对亚父范增还是有几分听从的。
陈平看准了这一点,他要做的,不是在战场上打败项羽,而是在项羽的心里,埋下一颗猜疑的种子,也就是要制造一种“你身边的人都不可靠”的“势”。
《史记·陈平世家》记载,陈平对刘邦说:
“项王骨鲠之臣,亚父、钟离昧、龙且、周殷之属,不过数人耳。大王诚能捐数万斤金,行反间,间其君臣,以疑其心。” 刘邦二话不说,拨出黄金四万斤,任由陈平使用,不过问具体用途。
陈平拿到钱,在楚军中大肆收买间谍,散布谣言,说:
“钟离昧等人为项王将,功多矣,然而终不得裂土而王,欲与汉为一,以灭项氏,分王其地。”
这个谣言非常高明。
它不是空穴来风,而是精准地切中了当时所有将领的共同利益诉求——封王裂土。
秦末乱世,无数人拼上身家性命,为的不就是这个吗?这个谣言,为楚军将领们“创造”了一个新的、看似更优的利益选项,从而在项羽心中,制造了一种
“手下大将随时可能为了利益而背叛我”的怀疑之“势”。
光有谣言还不够,陈平紧接着上演了一场登峰造极的“行为艺术”。
当项羽的使者来到汉营时,陈平故意准备了极为丰盛的筵席。
他一见使者,假装惊喜地问:
“我以为是亚父(范增)的使者来了,没想到是项王的使者啊!” 说完,立刻命人将丰盛的酒菜撤走,换上了非常粗劣的饭菜。
使者回去后,将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项羽。
项羽本就多疑,听闻此事,心中那颗猜疑的种子瞬间生根发芽,他对范增的信任,彻底崩塌了。
他开始相信,范增真的和汉军有私下的勾结。
“势”已造好,接下来就是顺势而为。
不久,范增敏锐地察觉到汉军的阴谋,急切地劝说项羽猛攻荥阳。
但此时的项羽,已经不再相信他了。
《史记》载:“项王疑范增与汉有私,稍夺之权。”
一代谋士,心灰意冷,对项羽说:
“天下事大定矣,君王自为之。愿赐骸骨,归卒伍。”
请求告老还乡。
项羽竟然同意了。
范增在返回的途中,“疽发背而死”。
陈平仅仅用了几万斤黄金和一场饭局,就兵不血刃地除掉了刘邦最忌惮的对手。
他用的,就是“造势”的阳谋。
他没有去刺杀范增,而是通过一系列操作,创造出一种“范增不忠”的假象,让项羽自己去怀疑、去疏远、去逼走范增。
他不是在和范增斗,他是在和项羽的疑心斗。
这就是顶级布局者的可怕之处。
他们不执着于一城一池的得失,而是着眼于整个大局的“势”。
他们懂得,人心之“势”,一旦形成,就像决堤的洪水,无可阻挡。
普通人看到的是桌上的饭菜,高手看到的是饭菜背后的人心。
普通人纠结于事情的对错,高手则思考如何引导他人得出“我想要的对错”。
所以,当你深陷困局,无“利”可趋时,不要灰心。
问自己几个问题:我能不能创造一种新的“势”?我能不能通过某些信息,改变对手的认知?我能不能让“潮流”推着我走,而不是我逆着“潮流”挣扎?
学会“因势利导”,你才能真正从棋盘上站起来,拥有拨弄棋子的力量。
藏器于身,待时而动:懂得“藏”,是布局的最高境界
我们已经谈了“趋利”、“避害”、“用势”。
但这一切,都有一个最终极的前提,那就是——“时机”。
再锋利的宝剑,若是胡乱挥舞,也只会伤到自己;再高明的计策,若在错误的时间使出,也只会沦为笑柄。
真正的布局者,都深谙一个“藏”字。
这第四个字,就是“藏”。
《周易》有云:“君子藏器于身,待时而动。”
“藏”,不是退缩,不是消极,而是一种极致的清醒和耐心。
“藏”的是你的锋芒、你的实力、你的意图。
在时机未到之时,把自己深深地埋藏起来,像冬眠的熊,像深潜的龙,默默积蓄力量,冷静观察时局。
直到那个最关键的“时机”出现,才如雷霆般一击而出,毕其功于一役。
《史记》中,谁最懂得这个“藏”字?不是刘邦,不是张良,而是那个前期看似毫无存在感,最后却窃取了曹魏江山,奠定西晋基础的司马懿。
司马懿的一生,就是一部“隐忍教科书”。
在曹操手下,他是被提防的鹰。
曹操曾做过“三马同槽”的噩梦,又见司马懿有“狼顾之相”,对他始终心存忌惮。
司马懿是怎么做的?他把自己的所有才华都“藏”了起来,表现得兢兢业业,勤勤恳恳,安分守己,从不结党,从不冒头,对曹操的任何指令都一丝不苟地执行。
他把自己伪装成了一只无害的、忠诚的牧羊犬,让多疑的曹操,终其一生都找不到杀他的借口。
这是对锋芒的“藏”。
在曹丕手下,他开始崭露头角,但依然极为谨慎。
他与曹丕、陈群等人共同推动“九品中正制”,为士族集团攫取了巨大的政治利益,赢得了根基,但他始终将自己置于曹丕的光环之下,从不居功自傲。
这是对功劳的“藏”。
到了曹叡时代,他手握军权,镇守雍凉,对抗蜀汉的诸葛亮。
面对这位旷世奇才,司马懿的策略只有一个字——“拖”。
无论诸葛亮如何挑战、如何辱骂,甚至送来女人的衣服羞辱他,司马懿就是坚守不出。
《史记》(此处应为《晋书·宣帝纪》,但为行文风格统一,仍借《史记》之名)记载,诸葛亮“数挑战,帝不出”。
司马懿深知,自己论奇谋巧计,不如诸葛亮;论军心士气,蜀军是哀兵远征,势在必胜。
但他有自己最大的优势——时间和国力。
他知道,诸葛亮北伐,粮草不济,拖不起;而他自己,背靠整个曹魏,拖得起。
他要做的,就是把诸葛亮活活拖死。
他在“藏”自己的兵力,更是在“藏”自己的决战意图。
他任由天下人嘲笑他怯懦,任由军中将领怨声载道,他自岿然不动。
最终,诸葛亮积劳成疾,星落五丈原。
司马懿不费一兵一卒,就赢得了这场长达数年的国运之战。
而司马懿一生中,“藏”得最深、最久、最惊心动魄的一次,是在他晚年。
明帝曹叡死后,曹芳继位,大将军曹爽与他共同辅政。
曹爽为了独揽大权,明升暗降,剥夺了司马懿的兵权。
面对权倾朝野、党羽遍布的曹爽,七十高龄的司马懿,再次选择了“藏”。
他称病在家,不问政事,彻底从权力中心消失。
曹爽派心腹李胜去探听虚实。
司马懿上演了影帝级别的表演:他假装老眼昏花,耳聋口齿不清,喝口粥流得满胸都是,把“荆州”听成“并州”。
李胜回去后,向曹爽报告说:
“司马公尸居余气,形神已离,不足虑矣。”
曹爽彻底放下了戒心。
而就在曹爽等人最志得意满,带着小皇帝出城去高平陵祭祀,整个洛阳城防务最空虚的那一刻——司马懿“动”了。
那个“病”得快要死的老人,在一夜之间,精神矍铄,目光如电。
他迅速关闭城门,占据武库,控制了整个京城。
等曹爽反应过来时,已成瓮中之鳖。
最终,曹爽集团被夷灭三族,曹魏的军政大权,彻底落入了司马氏的手中。
从称病到政变,司马懿“藏”了整整十年。
这十年里,他承受着屈辱,压抑着欲望,忍受着寂寞,只为等待那个唯一的机会。
这就是“藏”的威力。
它是一种动态的平衡,是在沉默中积蓄雷霆的力量。
不懂得“藏”,你的所有“趋利”、“避害”、“用势”,都只是小打小闹。
因为你的底牌,早已被人看得一清二楚。
真正的布局者,永远让人看不透。
当他沉默时,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;当他微笑时,你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
他永远像海面下的冰山,你看到的,只是微不足道的一角。
写在最后
行文至此,我们再回过头来看“趋利避害”这四个字,或许有了全新的理解。
趋利,是让你看清人性的底层代码,找到驱动万事的钥匙。
避害,是让你敬畏规则的边界,守住安身立命的底线。
用势,是让你超越眼前的得失,学会借用潮流的力量,无中生有。
藏器,是让你掌控自己的节奏,在沉默中等待雷霆一击的时机。
这四个层次,层层递进,互为表里,共同构成了《史记》中那博大精深的权谋智慧。
它不是教你诈,不是教你坏,而是教你看清这个世界的真实运转规律,然后用最高明的“阳谋”,去实现自己的目标,保护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。
城府深,不过是戴上了一副面具,看似神秘,实则脆弱。
一旦被人看穿,便无所遁形。
而真正懂得“趋利避害”这四字真言的人,他们或许看起来温和、普通,甚至有些“迟钝”,但他们的内心,却如同一片深邃的大海,看似平静,实则蕴含着足以改变一切的力量。
他们不与小人争口舌之利,不与时势逞一时之勇,他们只是在自己的时区里,不疾不徐,向着既定的目标,稳稳地走好每一步。
愿我们,都能从司马迁留给后世的这部伟大史诗中,汲取到这份穿越千年的智慧。
从今天起,学着去做一个清醒的观察者,一个耐心的潜藏者,一个懂得顺势而为的聪明人。
当你真正读懂了利益的流向,敬畏了风险的边界,掌握了趋势的密码,并拥有了等待时机的耐心,那么,你的人生棋局,将由你自己,亲自来布局。
配资炒股平台入配资,配资实盘平台排名前十,十大配资公司排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查询使肌肤回复光滑与弹性
- 下一篇:配资门户导航双十一叠加满减和折扣后